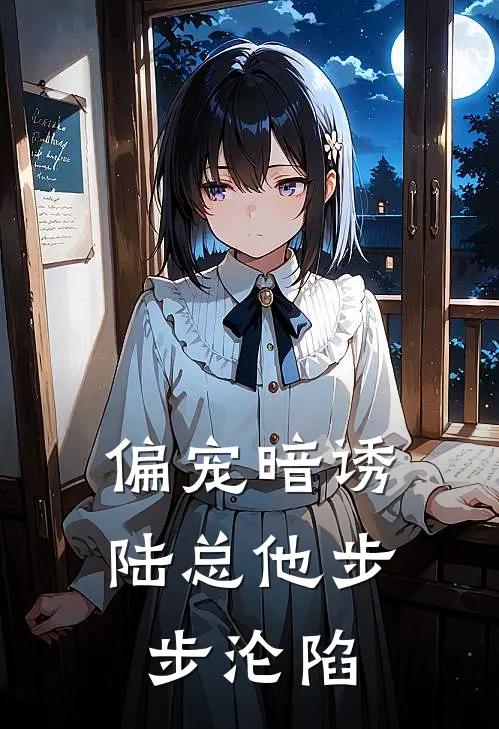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金牌作家“宿山水”的古代言情,《陋室长铭之我和我的养父刘禹锡》作品已完结,主人公:柳周六柳宗元,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:,大唐元和十四年,冬。,炭火将熄未熄,余温在深冬的寒意中节节败退。药气沉甸甸地压在空气中,混合着陈年木料与旧书卷的霉味,像一层看不见的纱幔,裹住了榻上那个只剩一息尚存的人。,自已等不到开春了。,从长安意气风发的进士、监察御史,到永贞革新时的礼部员外郎,再到这岭南蛮荒之地的刺史。半生漂泊,半生困顿。他的视线已经模糊,却仍能透过半掩的窗棂,看见院中那株亲手种下的柑橘树——枝叶凋零,在北风中瑟缩着,一如...
,唐元和年,冬。,炭火将熄未熄,余温深冬的寒意节节败退。药气沉甸甸地压空气,混合着陈年木料与旧书卷的霉味,像层见的纱幔,裹住了榻那个只剩息尚存的。,已等到春了。,从长安意气风发的进士、监察御史,到贞革新的礼部员郎,再到这岭南蛮荒之地的刺史。半生漂泊,半生困顿。他的已经模糊,却仍能透过半掩的窗棂,见院那株亲种的柑橘树——枝叶凋零,风瑟缩着,如他未竟的抱负。“周……”。,个岁的身跪蒲团,紧紧攥着身粗麻孝衣的摆——那是前备的。孩子低着头,清,只露出个薄的、颤的肩膀。,喉间涌阵酸楚的腥甜。周,生于元和年,因是出而取名。这孩子弱,子也安静得过,似寻常稚童那般吵闹。此刻跪那,竟有种越年龄的沉寂。
他知道的是,这具的身躯,此刻正经历着怎样地覆的变。
疼。
头像是要裂样疼。
柳明哲后的记忆,是实验室刺耳的警报声,以及那道失控劈来的弧光。他是研究古文献数字化保护的工程师,那晚正调试新设备,试图更准地还原唐写本的笔触与墨。
然后便是暗,漫长而混沌的暗。
再睁眼,刺入感官的先是刺鼻的药味,接着是深入骨髓的寒意。他发已跪冰冷的地面,低矮,得像话——那是孩童的。
数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冲入脑:柳周,岁,父柳宗元,母早亡……元和年……柳州……
柳明哲,,他是柳周了,猛地抬起头。
眼前是张古旧的木榻,帷帐半垂,榻躺着个消瘦的年文。面容枯槁,颊深陷,唯有那眼睛,即便生命将尽的刻,仍燃烧着某种难以熄灭的光。
柳宗元。
学课本那个写《江雪》《石潭记》的文。那个“山鸟飞绝,万径踪灭”的孤背。那个历史,即将这年冬病逝于柳州的柳宗元。
实的、有温度的、正死去的历史。
柳周感觉身的血液都冻住了。他是阅读文献,是虚拟实验历史场景。他正跪柳宗元的病榻前,穿着前备的孝衣,而榻的……是他的父亲。
“周。”柳宗元又唤了声,声音弱却异常清晰,“近前来。”
柳周几乎是机械地挪动膝盖,靠近沿。他仰头着这个陌生的、却又血脉深处感到亲近的男,喉咙发紧,个字也说出来。
柳宗元艰难地抬起枯瘦的,轻轻幼子的头顶。那只很凉,却带着种奇异的、沉甸甸的重量。
“为父……多了。”
柳周的眼泪毫预兆地涌了出来。这完是他的绪,是这具身原主的悲恸,是血脉亲的本能,也夹杂着他作为个闯入者面对历史重量的震撼与茫然。
“莫哭。”柳宗元的指尖拂过孩子的脸颊,拭去泪水,动作温柔,“男儿立,当……当有泪轻弹。何况……”他顿了顿,喘息几,才继续道,“吾儿虽幼,却要记着,你姓柳,是河柳氏之后。”
河柳氏。那个“河凤”的家族,那个曾与薛、裴并称“河著姓”的家。如今,只剩这柳州官舍的缕残灯,个将死的父亲,和个岁的孤雏。
窗来更鼓声,沉闷而遥远。,深了。
柳宗元的目光向虚空,仿佛穿透了屋顶,向更的方向。“为父生,憾事良多。憾者……能见你长,能亲授你诗书经义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,随后又猛地凝聚起后的气力,紧紧攥住了柳周的。
“但有事,为父……为你谋了条生路。”
柳周屏住呼。
“我已修书……给你的刘伯父,刘禹锡,刘梦得。”柳宗元的眼闪过复杂的光,那是追忆,是舍,是托付切的决绝,“我与他……同榜进士,同道革新,同贬远州。他是这……知我、亦能托付之。”
刘禹锡。那个写“沉舟侧畔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诗豪。那个历史,确实抚养了柳宗元幼子的。
“他来。”柳宗元说得异常肯定,仿佛用尽了毕生的信念支撑这个预言,“待他来,你便随他去。之如父,听之如师。”
他的颤得厉害,却将柳周的握得更紧,几乎要捏碎那的指骨。
“听着,周,此乃为父后嘱托——”柳宗元字顿,每个字都像用刻刀凿进空气,“子厚之文脉,吾儿之命,皆托于刘梦得。”
文脉与命。
柳周浑身震。他听懂了这句话泰山压顶般的重量。那只是个父亲托孤,更是个士、个思想家、个文化的承者,生命尽头,将的火种与血脉的延续,重托付给信的挚友。
这是历史的托付。
柳宗元说完这句话,仿佛后的气力也随之抽空,整个瘫软去,唯有眼睛仍死死盯着儿子,那目光有言万语,有未尽之志,有深沉的、法言说的父爱。
“阿耶……”柳周终于发出了声音,稚,嘶哑,带着哭腔。
柳宗元的嘴角其弱地向牵动了,似乎想挤出个笑容。他的目光始涣散,终,缓缓闭了眼睛。那只紧握的,点点松,滑落。
炭火盆,后点猩红的光挣扎着闪烁了,彻底熄灭。
寒风从窗隙灌入,吹得案头未写完的书稿哗啦作响。烛火猛烈摇曳,墙而动荡的子,终,归于沉寂的暗。
柳周跪彻底冰冷的榻前,维持着原来的姿势,动动。
前的记忆,今生的实,历史的洪流,个的渺……所有的切他岁孩童的脑冲撞、轰鸣。他能感觉到脸颊未干的泪痕,能听到已脏胸膛狂跳的声音。
穿越了年的空,他为了柳周。
而历史,正以实、残酷、沉重的姿态,碾过他的生命。
窗,柳州城飘了这个冬的场细雪。雪花声息,覆盖着南陌生的山峦与江水,也覆盖着个伟灵魂逝去的这个晚。
远处,隐约有蹄声方来,踏碎风雪,正昼兼程。
刘禹锡,要来了。
柳周缓缓抬起头,望向边的暗。他知道,从这刻起,他再是的柳明哲,也再是的柳周。
他是托孤的遗子,是文脉的继承者,是这场穿越谜局,枚刚刚落历史盘的、足道,却可能改变路的子。
漫漫长,刚刚始。